似乎在今天的职业世界中,一个人想要在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里找寻到“意义感”已经变得越来越奢侈,甚至很多人会退而求其次:
工作而已,不必上头;
有工作就不错了,还谈什么意义;
工作本来就没什么意义,挣钱养活自己就是意义……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每周至少有5天需要工作,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花在工作上。我们一边告诉自己“要想开”,一边又的确很难放下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不快不爽。
如果你也会因工作而感到倦怠无力,想躺平又难平,欲佛系而不能,求意义却不得,不妨读读这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英文名:Bullshit Jobs: A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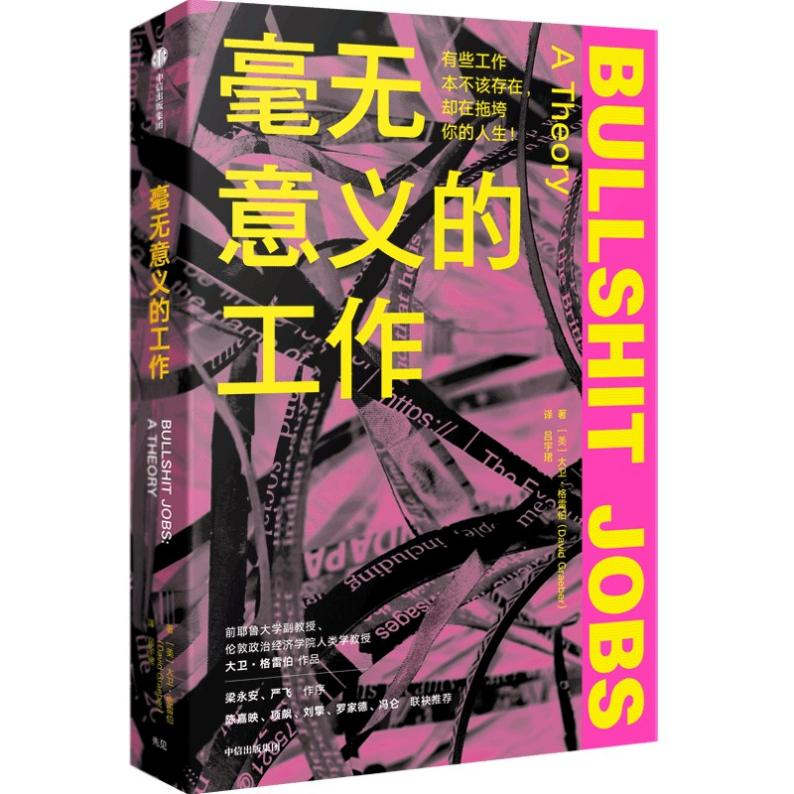
这本书的作者大卫·格雷伯,生前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一位慷慨激昂的人类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曾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参与者)。
因为格雷伯凭着他敏锐的直觉,以非常精辟的文笔描绘了他所观察的无意义工作的社会乱象1,令来自世界各地的职场牛马们纷纷拍手称赞并积极参与吐槽2;
而人们的讲述又给格雷伯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和便捷的田野路径,让他得以进一步通过访谈建立起更为详实的“狗屁工作”内容库,并基于此对“狗屁工作”现象来了个全方位、有深度的剖析,就形成了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
读它,你的情感会在来自全球范围的职场人士的吐槽中感到深深的共鸣,你的心灵会在作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得到彻底的释放。
当负面的情绪通过读书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方式得到抒发,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获得了力量,可以真正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离有意义的工作更近一点了——毕竟,不论是为了个体的幸福还是社会的福祉,我们都不能轻易放弃对工作意义的寻求。
01.“狗屁工作”的定义和五种类型
什么是“狗屁工作”?
格雷伯给出了他的定义: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p.013)
他又接着将狗屁工作具体分为五种类型:
1.随从(flunky)。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是主要目的,就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为数不多的具体的任务也只是为了显示这个岗位存在的合理性。
格雷伯的案例提供者之一杰克,是一位证券交易公司的电话推销员,工作内容是给别人打电话推销股票。不过,这家公司在内部开展推销业务培训的时候,最注重的并不是如何才能把股票推销出去,而是要求推销员一定要记得向对方强调“我是代表某某股票经纪人的”。因为这样可以向潜在客户塑造出经纪人的光辉形象:这位经纪人竟然忙到需要一位助理来帮忙打电话,那一定是业务能力非常出色了。
所以,杰克表示:“我在这个公司的岗位是多余的,除了让我的上级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或者看起来像个大人物,没有任何作用”。这就是“随从”。
2.打手(goon)。打手是个隐喻,它并不是指被雇来打人或伤人的工作,而是指具有一定操纵性/攻击性和欺骗性的,但存在的根本原因不过是因为有人花钱让它存在的那些岗位。典型的打手岗位,包括各种游说者,行销大师、公关人员、企业律师、推销员等等。
格雷伯说自己也曾做过类似打手的工作,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事情,能比让你昧着良心劝服别人做有违他们自然判断的事情要来的更加令人不爽了”。而这些工作如果全都消失,其实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任何负面影响。
3.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这类岗位完全是为了应对系统或组织的某个故障或缺陷而存在的。当系统出现了某种故障,人们不会直接想办法解决掉这个故障本身,而是设置岗位来修补因为这个故障而导致的其它各种新问题。
典型的拼接修补者来自软件行业,有一位软件工程师说:
“我们主要有两种工作。一种是致力于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各类难题的攻克。另一种是把现成的几项核心技术拿过来一通拼接,实现各项核心技术的合体”。(p.050)
程序员们都知道第一种工作更有用、更令人满足,但之所以出现第二种工作,就是因为做核心技术的程序员并不会考虑这项核心技术能不能与其他人开发的程序相兼容。在核心任务完成之余,总是会有“烂摊子”需要人收拾,而这就是拼接修补者精神苦痛的来源:
他们的全部工作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但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压根儿懒得管这些。
格雷伯还做了个类比,他说这就好像房顶漏水了,但房主觉得找个专业人士把屋顶修好太麻烦,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了个人,全职照看这个水桶,定期把水桶的水倒掉。
4.打钩者(box ticker)。打钩者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他们的组织可以对外公开宣称,他们正在做某件其实没有真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专职的“打钩者”在为这件事情做记录。
怎么理解呢?格雷伯举了个在疗养院工作的女士的例子,她说:
“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询问这里的住户他们的业余爱好,然后把问到的结果填到表格里,再把表里的内容输到计算机里,之后这些内容马上就被人永远遗忘了。……如果我没及时完成这些表格的工作,我就死定了。……我的询问只会引起住户的反感,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不过是文书工作,并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p.056)
这个工作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打钩者知道自己的工作所浪费的,就是原本可以投入在这些事务上的时间和资源。疗养院女士花在住户爱好表格上的时间,恰恰就是没有花在住户爱好上的时间。这类工作的纸上记录的现实比真正的现实世界更重要。
还有一个看上去更“精英”的打钩者工作,就是为公司撰写非常漂亮的PPT和报告(p.60);不论是在公司内部为管理者写项目报告或者演讲PPT,还是为其他公司提供各种咨询报告,都只是在“打钩”,没人会真的仔细看,也不会真的去执行这些业务——报告提交了,工作就完成了。
5.分派者(taskmaster)。分派者的工作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别人派活,但其实如果没有他派活儿这一步呢,下面的员工也都能把活干完干好。这和第一种“随从”刚好相反——随从是没必要存在的下级,而第一类分派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上级。
第二类分派者比第一类还要“更进一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出来各种无意义工作分派给别人做,然后还要监督他们完成这些无意义工作。
这里格雷伯举了个他所知道的从事第二类分派者工作的案例,是英国某大学的“战略指导”。这位战略指导要给各个部门、各项业务提出各种战略愿景的策略方案,但是她很清楚自己并不属于领导层,她没有实权,也没有预算用来推进这些战略。所以,她只是费劲心思地安排自己的下属(包括一位个人助理、一位业务支持专员和一位博士后研究员)一起辅助她完成一系列不会有人依照执行的“战略方案”。
在这五种基本类型基础上,还有一些是复合型的无意义工作和次级无意义工作。
复合型无意义工作就是同一个岗位同时具备以上某几种工作的特质。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大学战略指导是一种分派者岗位,需要制造各种“战略任务”去给自己的下属派活。换个角度,这位战略指导也可以说是“随从”,因为设立这个岗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大学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只写方案无须执行的“指导”,而是真正的领导在地位象征的层面有需求。在实际工作中,其实他们也没有多少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又会作为“拼接修补者”去给其他工作搭把手。
还有一种典型的复合型无意义工作是“投诉接收”岗位,就是专门应对和处理客户投诉的工作者。格雷伯的点评也很犀利,他说其实很多投诉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之所以设置这个接收投诉的岗位来应对客户投诉,恰恰是因为这些投诉接受者完全没有任何权限去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既是一种给公司主要业务收拾烂摊子的拼接修补者,也是可以衬托公司和管理层形象的“随从”——这家公司有专门的客户服务部门!
那什么叫做“次级狗屁工作”呢?就是其实这个工作本质上不能说是无意义的,但它们最终服务于那些无意义的狗屁工作。比如那些从事无意义工作的公司的清洁工、维修人员等等。
02.为什么从事“狗屁工作”让人不快乐?
格雷伯在分析各种“狗屁工作”的案例时,发现一个略显奇怪的悖论:很多为他提供素材的受访者,其实都从事着所谓“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好工作”。但这些人不仅为此痛苦,而且还非常困惑:为什么这个工作会让自己感到一无是处甚至陷入抑郁呢?钱多事少的“理想工作”也可能会是一种“狗屁工作”吗?
格雷伯认为,出现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通常都会默认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成立的:一个人,只要拥有自主支配权,就一定会采取消耗最少但收益最大的行为。换句话说,只要是个人,就想少干活多拿钱。
但不分情境地默认这一假设的成立,可能正是我们对人类做事动机的一种全然的误判。“哪怕最自私的人最终也会发现,比起辛苦万分还不赚钱地劳作,整天坐着啥都不干而只看电视的命运会让人更难以忍受。”(p.098)
怎么理解这件事呢?格雷伯引用了20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的一项研究。格鲁斯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而这种影响是什么,以及对婴儿是否有益,都跟这份开心毫无关联。”
格鲁斯把这个叫做“身为原因的快感”,这种快感就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这个权力我们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它其实就是婴儿在察觉自我存在的过程——婴儿是在觉察到自己是某事发生的原因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我存在的。
所以,选择去从事一项工作,一种最简单、最本性的动机就是:我想要施展自己的能力,想要让自己的行动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点影响。按照格鲁斯的说法,这就是自由之所在。当然,工作需要达到挣钱的结果,需要有舒适的环境,需要有体面的地位,等等……但除却这些外在的好处,我要通过工作、通过对我所处的世界产生一点影响,来感受自己的存在。
某些钱多事少的工作会带给人痛苦、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就是因为他们拿着薪水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公司里有没有自己,重要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少了自己,一切照常。格雷伯如是说:
“雇佣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p.100)
所以对于工作,我们一定会在乎什么呢?我们一定会在乎的,是我的行为能对世界产生哪怕一点点的积极的影响。这是人性使然,是自我之存在、自由之所在。
而狗屁工作之所以会让我们嗤之以鼻,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在这项工作中看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点影响。
狗屁工作让人不快乐的另一个原因,和“花钱买时间”的现代观念有关。
格雷伯指出,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大家认为的正常工作模式,就是“有规律地一阵猛干,然后休息,恢复之后进入新一轮猛干”。比如农活:
“农忙时期,调动所有人手,全力投入;农闲时期,大部分时候人们的工作就是些照料和修修补补的货,偶尔有些小工程,其余便是到处闲逛了。”(p.102)
又比如,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在浴血奋战和安逸懒散之间来回切换,而农民和仆人的工作虽然比起封建领主要规律得多,也没有现代人每天“朝九晚五”那么严格。
但进入现代社会,当时钟和怀表逐渐进入家家户户,当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展,人们也逐渐从“用行为测量时间”变成“用时间去测量行为”,让这个由天体决定的“绝对时间”开始控制管理人类的日常事务。
人们可以用统一的单位对时间进行切割和买卖,开始用“花费”这个动词来搭配它,而不仅仅使用“流逝”。诸如“浪费时间”“节约时间”“打发时间”等等一系列的说法也开始出现。
在西方,教会的布道者也开始教导信徒们“精打细算着使用时间”,“对时间的合理规划和使用正是道德的本质”(p.107)。随着时间观的革新开始具有道德意味,“旧有的那种松散随意的、忙闲交替的工作方式越来越被视作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于中产阶级开始觉得“穷人之所以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够自律,没有时间观念”(p.108)。
时间久了,工人自己也不得不用同样的说法来抗议自己的糟糕处境:他们向工厂主要求固定的工作时长和更高的时薪,这样的反抗恰好潜移默化地加强了时间购买的观念:
“当工人‘开始进入上班时间’,他的时间就确确实实属于老板了,老板‘买’下了他的上班时间”。(p.108)
时间观的变革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它会与人们长期以来自然的工作节奏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就发生在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当时间可以被买卖后,雇佣者眼中的道义就是“我购买了你的工作时间”,“我花钱不是用来养闲人的”。但被雇佣者一以贯之的下意识,往往是“我的职责是把分内的工作做完”。一个简单的例子:
格雷伯讲到自己儿时暑假曾经在一所餐厅兼职做洗碗工,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在餐厅爆满时从容应对,洗完了一波又一波数量惊人的碗。忙完后的休息时分,他们正回味刚刚取得的成就,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洗碗工而得意时,就被老板发现了:
“你们为什么在偷懒?我不管现在有没有碗需要洗,你们现在的时间就是我的,都给我回去工作!”
“那现在做什么?”
“去把踢脚线都给我刷亮了!”
“可是我们已经刷过了。”
“那就再刷一次!”(p.109)
于是格雷伯和他的洗碗工伙伴们就吸取了教训:工作效率不要太高。因为一旦空出了时间,就不得不做些毫无意义的假模假样的工作。
而且,因为现代社会从法律和道德上都支持“工作时间的购买”——劳动合同书会标明八小时工作制,社会道德推崇自律而不是懒散——那种原本不需要存在的工作岗位例如打钩者、拼接修补者、分派者等等就会被发明出来,因为公司不养闲人。
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就并不好受了。他们先是被监控着有没有在工作时间偷懒,然后又被权力要求着去做与职责本身无关也看不到任何意义的各种事务来“假装工作”,以便让自己看起来一直在忙于工作。
哪怕这其中有许多人拿着固定月薪也没有上级盯着他们在做什么,这样假装工作也容易让人意志消沉,不只因为“没意义”,也因为它是权力压迫而非自主选择的结果。
格雷伯总结,被外力迫使去做一些对世界和他人没有任何积极影响的工作,这样“装模作样的游戏”:
“好似把领薪工作中最糟糕的点拎出来,填进那些原本应该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的职业之中。难怪灵魂都在大声哭泣,那些使我们作为人类而存在的根基全都被动摇了。”(p.116)
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为这本书的上半部分做一个小结:狗屁工作有很多种类型,而它们之所以让人痛苦,都是因为“毫无意义”。而在格雷伯搜集来的各种狗屁工作案例中,我们也能反观,怎样的工作才会让人觉得有意义:
一是自己的付出可以为世界和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二是自主选择的权利。
它们的共性是,都能让人感觉到自己生而为人、存在于世。
本文为《毫无意义的工作》推荐第一篇。下一篇将继续解读本书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作者格雷伯先深入剖析毫无意义的工作所带给人的具体的痛苦,再从个体的痛苦扩展到历史与社会的维度:
我们面临怎样的社会现实,使得今天的人们只在个体层面私隐地吐槽工作本身,却几乎不从社会层面公开讨论和反思无意义工作激增的现状与风险?
工作的无意义化为何需要受到更多的重视?它可能会引发怎样的社会后果?提出“狗屁工作”的作者格雷伯本人认为可以如何应对?
敬请期待。
注释:
1.2013年,格雷伯接受《罢工!》杂志的邀请,发表了《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
2.此文发表后迅速被译为十多种语言转发在不同国家的各种报纸及博主网站上,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
作者: Savannah
编辑:果子、苏木
图片来源:网络
电话:010-58804184
邮箱:tianxing@bnu.e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富中通和大厦10层1002

微信公众号天行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