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最大的错谬使之沦为神性的囚徒,那么列维纳斯的海德格尔则可能是意义的奴隶。在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对人之处境最大的误解是令社会性植根于孤独,并附属于本真。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处界定即是“肩并肩”与“面对面”的区分:面对面能够形成无待外求的主体间性,但海德格尔的“此在”之间的关系恰只是肩并肩的——这样的主体们在联合之时总是共同面向某种外在的意义或目的指向,服从于本质和本真,并在这一处境中既遗失了他者,也遗失了自我。用列维纳斯自己的话说,肩并肩的“此在”群体共同追求着“在其本真形式中解蔽的真理”,致使伦理关系的重要性让位于存在论,其根源可追溯至西方哲学之始:
而海德格尔恰恰继承了这种关于集体-社会图式的柏拉图主义:“共/与在也保留着与(avec)的集体性,它围绕着在其本真形式中解蔽的真理。……就像在所有共契(communion)的哲学中一样,社会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在孤单的主体中被发现的,并且通过有关孤独的诸概念,延续着对在其本真形式中的此在的分析。”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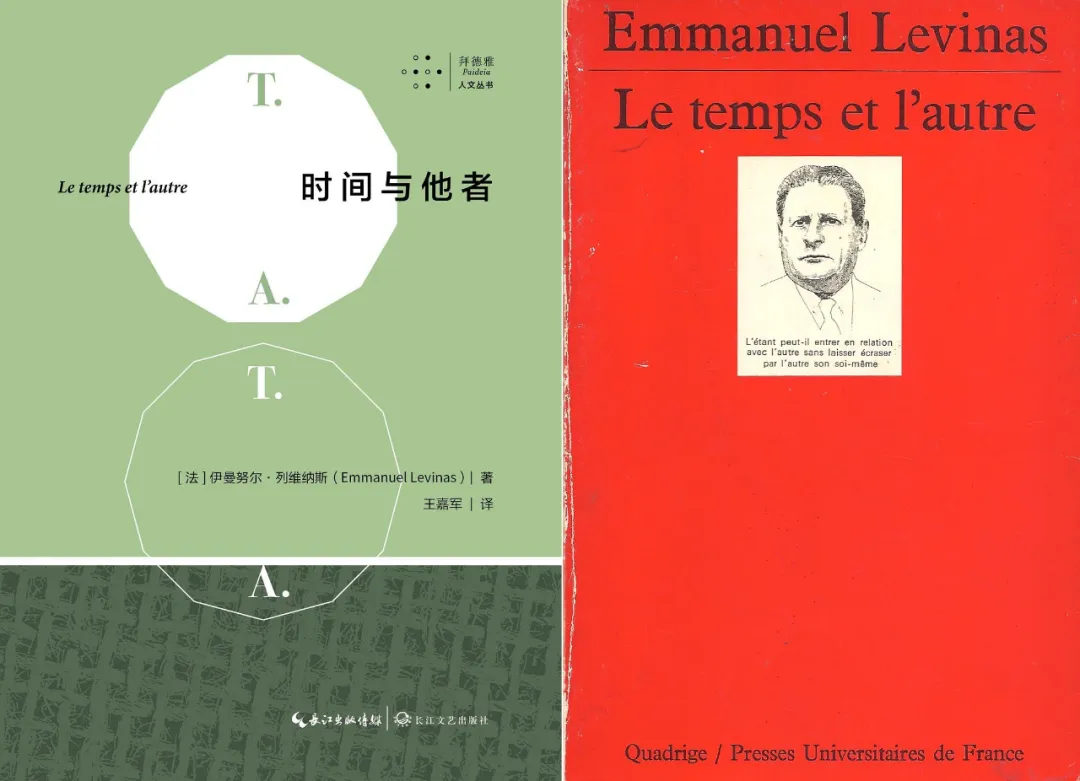
与之针锋相对,列维纳斯吁求一种不借助“第三项”的“没有中介的面对面”,无论我们所能想象的第三项“是一个人、一种真理、一种工作,还是一门职业”。惟其如此,我们才有望获得“一种朝向将来之神秘的现在之时间性超越”3。以此为据列维纳斯构建了别一种第一哲学,即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据概括,传统第一哲学通常是形而上学或神学;海德格尔的第一哲学是存在论,他称之“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是关于此在之存有的理论;列维纳斯同样志在第一哲学,但他的第一哲学是伦理学4。
列维纳斯的第一哲学既批评海德格尔的共在论(如上),又反对海德格尔的死亡观。“向死而在”之论不仅就结果而言将死亡强调为一种解放(如阿伦特已经指出的),而且就过程而言在死亡中放大主体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列维纳斯将要指出的):“向死而在,在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实存中,是一种极度的明澈性并且因此是一种极度的男子气概。它是此在对实存最终的可能性之承担,它使得所有其他可能性成为可能,……它使得能动性和自由成为可能。死亡在海德格尔那里是自由的事件”。5
然而对列维纳斯而言,死亡使得主体陷入全然被动,使得主体不再是主体,而且,死亡在时间中具备全然未来性(非当下性):死亡“是一种主体的被动性经验”,昭示了“一种主体不再是掌控者的事件,一种与之相关,主体不再是主体的事件”;换言之,“主体似乎在受难中达到了其可能的极限”,在此极限下“它发现它自己以某种被动的方式,被束缚了、被溢出了”,并且达于“观念论的界限”——死亡遂成为“某种绝对不可认识之物”,并且“标示着主体的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之终结”6。在时间中,主体的掌控者身份关联于其当下性,与之相对,死亡绝无当下性:“当下(lemaintenant)意味着我是掌控者,可能性之掌控者,把捉可能性之掌控者。死亡从不是当下。”7
于是与向死而生大有不同,列维纳斯式的主体与死亡的关系是“与神秘的关系”,而所谓神秘,意思是“主体与一种不是来自自身之物发生关系”,并因“抵触自身和自我之间的亲密性(intimité)”而痛苦8。由此反倒展开了新的理论希望,因为若牢记“不是来自自身之物”这个界定,就很容易推知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同样是与神秘的关系(于是亦可借助对他者问题的统一解决而应对死亡问题),列维纳斯也正是由此出发讨论他者问题并构筑其伦理学大厦,这也就回应了他本人的理论承诺:“海德格尔的著作……是现代哲学一个关键却危险的阶段”,但是,“要摆脱他的思想局限,就要彻底地思考和超越他,而不是回到海德格尔之前那种令人舒适的天真状态”9。
在他者问题上拒绝天真,列维纳斯直接摈弃了“和谐”与“同情”之类前海德格尔式理解,从而能够讨论一种后本真的社会性。他强调:“他者不是任何形式的另外一个自我本身(un autre moimeme):其与我一起分担一种共通的实存(une existence commue)。与他者的关系不是一种田园诗式的和谐的共通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同情,通过这种同情我们把自己置于他者的位置,我们认识到他者类似于我们,却外在于我们;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与‘神秘’的关系。”。10
即是说,列维纳斯与阿伦特不同,并未站在反对孤独、反思本真的相异立场上与海德格尔的此在自我图式对抗。阿伦特的共和主义式社会理想仍显然有赖于列维纳斯在上述断言中所摈弃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通或设身处地(即同情)。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出发点一致,与阿伦特有别——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与超越从而是后本真的,而非反本真的。
参照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列维纳斯刻画了一种向死而共在:“一个存在,只有已经通过受难而到达孤独的紧张状态,并处在与死亡之关系中,才能置身于一块在其中与他者的关系变得可能的领地。”11然而参考对死亡处境已经做出的描绘,这种“向”死而共在仍然只是关于被动性的纯然想象,它只是为了强调我们无法理解他者正如同我们无法理解死亡,强调他者与死亡共同的未来性:“有可能从这种死亡的情形中——在其中,主体不再有任何把捉的可能性——提取出与他者[关系]之实存的另一个特征。没有任何办法把捉的东西就是将来,将来的外部性与空间的外部性完全不同,这正是因为将来是绝对的出乎预料。……将来是不可把捉之物,是不期而遇地降临于我们并抓住我们之物。将来,就是他者。与将来的关系正是与他者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谈论一种在孤单的主体之中的时间,或者谈论一种纯粹个人化的绵延,是不可能的。”12
那么自动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主体如何如承担死亡般“承担”他者,而不致被“压碎”?既然他者即将来,有着全然时间上的“外部性”,主体将如何抵达之、甚至“掌控”之?13正是神秘的物事——例如死亡,例如他者——能够“给孤独开启了一个出口”;而“进入一种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却并不使得它自身被他者所压碎”这一问题,所回答的“正是自我在超越中的保存这一难题”。
如是,列维纳斯的他者问题将我们所关注的几乎全部主题——绵延与本真、他者与关系、超越与保存等——尽数统摄其中。那么,与他者的关系如何成为主体间关系?这与时间上将来如何介入现在是同一问题:列维纳斯首先明确了“‘被承担’的他者就是他人”;其次,“与将来的关系,将来在现在的出场,看上去都已经在与他人的面对面中被完成了”;但这种被完成的关系,无论视其为与将来还是与他人,都“既与存在主义,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完全不同”14。
紧接着那句“被完成”之论,列维纳斯预先摆出一段颇为难解的结论:“面对面的情形将是时间的完成本身,现在对将来的侵越不是孤单的主体的成就,而是一种主体间关系。时间的条件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或位于历史之中。”15展开这一论述时,列维纳斯将他者-他人问题的解答譬喻为父子关系,因为时间的本质“还是一种新的诞生”,而不只是“质性的更新”:在此,他基于却超越了柏格森所坚持的“绵延就是创造”,将之批评为一种“不含死亡的哲学”,因为通过创造实现的更新“依旧附属于现在”,但创造本身就还“预设了”一种朝向“神秘”、因而是朝向将来的“敞开”。16
列为纳斯在他者-他人问题(即关系问题,亦即伦理问题)上最根本的自问自答是:“在你(un toi)的他异性中,我如何能够保存自我,而不被你所吸收,或丧失于你之中?自我如何在你中保存自我,然而又不是在我的现在中我所是的那个自我,即命中注定回归自身的自我?自我如何变得他异于自身(autre à soi)?这唯独能以这样的方式发生:通过父性/父子关系(la paternité)而发生。”17
“父性”概念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提示了一种最本己的陌生人的可能:据列维纳斯的定义,“父性是一种与既全然作为他人、却又身为我的陌生人的关系”,即,它是“是自我和自我-本身(moi-même)的关系,这个自我-本身却又是我的陌生人”18。这种“父子关系”中,我占据父性,而作为关系相对者的“子”既不是“我的作品”,也不是“我的财产”,还不是“是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而是“一个自我”、“一个人”:我并不拥有该子,甚至“某种程度上就是”该子。这里的“是”作为一个独特的词被列维纳斯强调出来:“在这一实存的动词中有一种多样性和超越,这种超越哪怕在最大胆的存在主义分析中都是缺乏的”。19
以父性解释超越,从而也就把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概念超拔至另一层次:如前所论,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概念并未考虑死亡,而是首先“朝向一种非个人化的泛神论”,从而无法“充分注意到主体性的蜷缩(crispation)和孤立”;但对列维纳斯来说,主体性的蜷缩和孤立却不可或缺,据此,“父性不只是一种父亲在儿子中的更新,也不只是一种父亲与儿子的融合,它更是父亲相对于儿子的外部性,一种多元论的实存”。请记起前文曾引述的时间中指涉将来的这种“外部性”,这意味着主体间的“关联”无所谓“融合”,而是恒常的“缺场”:
由此回到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最根本批评,从主体之本真性的孤独/孤立出发,最为真实的主体间关系模式甚至不是爱欲——尽管列维纳斯真正堪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齐名的最流行格言或许是“爱如死之坚强”(可另文梳理)——而是父性。正是这种关系替代了海德格尔那种“肩并肩”的仍须围绕外在“第三项”之牵引方可稳固的修正的古典集体性。值得另文梳理的另一处概括来自列维纳斯的另一部著作,以免父性/父子关系这一过于形象的概括影响我们把握列维纳斯关于他者及社会性问题的更深刻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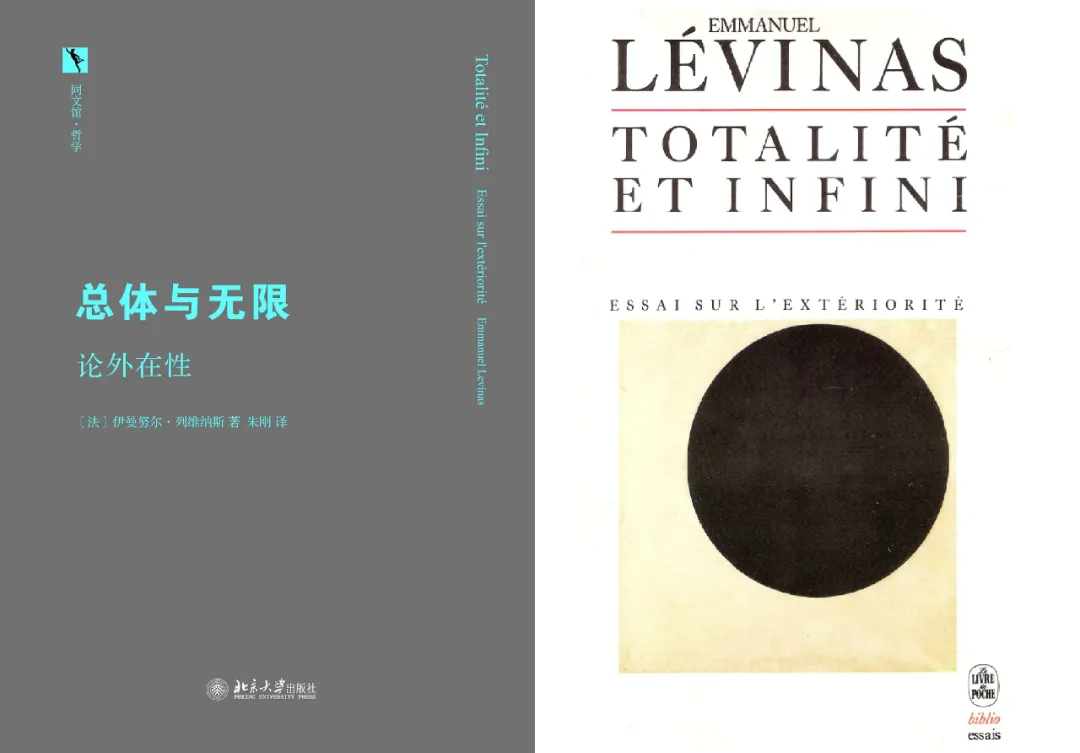
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总体性,以及这种能够作为“第三项”的总体性对他人和我、以及我们的集合体的共同召唤。在海德格尔的局限中,不得不处于肩并肩关系的注目于同一外在方向的自我与他人都将注定受那种被列维纳斯拒斥的第三项的役使。
注释:
1.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0-91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2.同上,第91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黑体强调为原文所有。
3.同上。
4.可直接参考斯坦福哲学百科“列维纳斯”词条: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evinas/
5.同上,第55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黑体强调为原文所有。
6.同上,第54-57页。
7.同上,第57页。
8.同上,第54页。
9.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研究者在这句概括中所讨论的“关键却危险”,特定围绕的恰是海德格尔“本真性”概念。
10.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第62-63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11.同上,第63页。译文有改动。
12.同上,第63-64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13.同上,第65-66页。
14.同上,第67-69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15.同上,第69-70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16.同上,第72-73页。
17.同上,第87页。
18.同上。译文有改动。
19.同上,第87-88页。黑体强调为原文所有,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20.同上,第88-89页。
21.同上,第85-86页。
22.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黑体字与着重号均为原文所有。
作者:朱泙漫
编辑:苏木
电话:010-58804184
邮箱:tianxing@bnu.e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富中通和大厦10层1002

微信公众号天行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