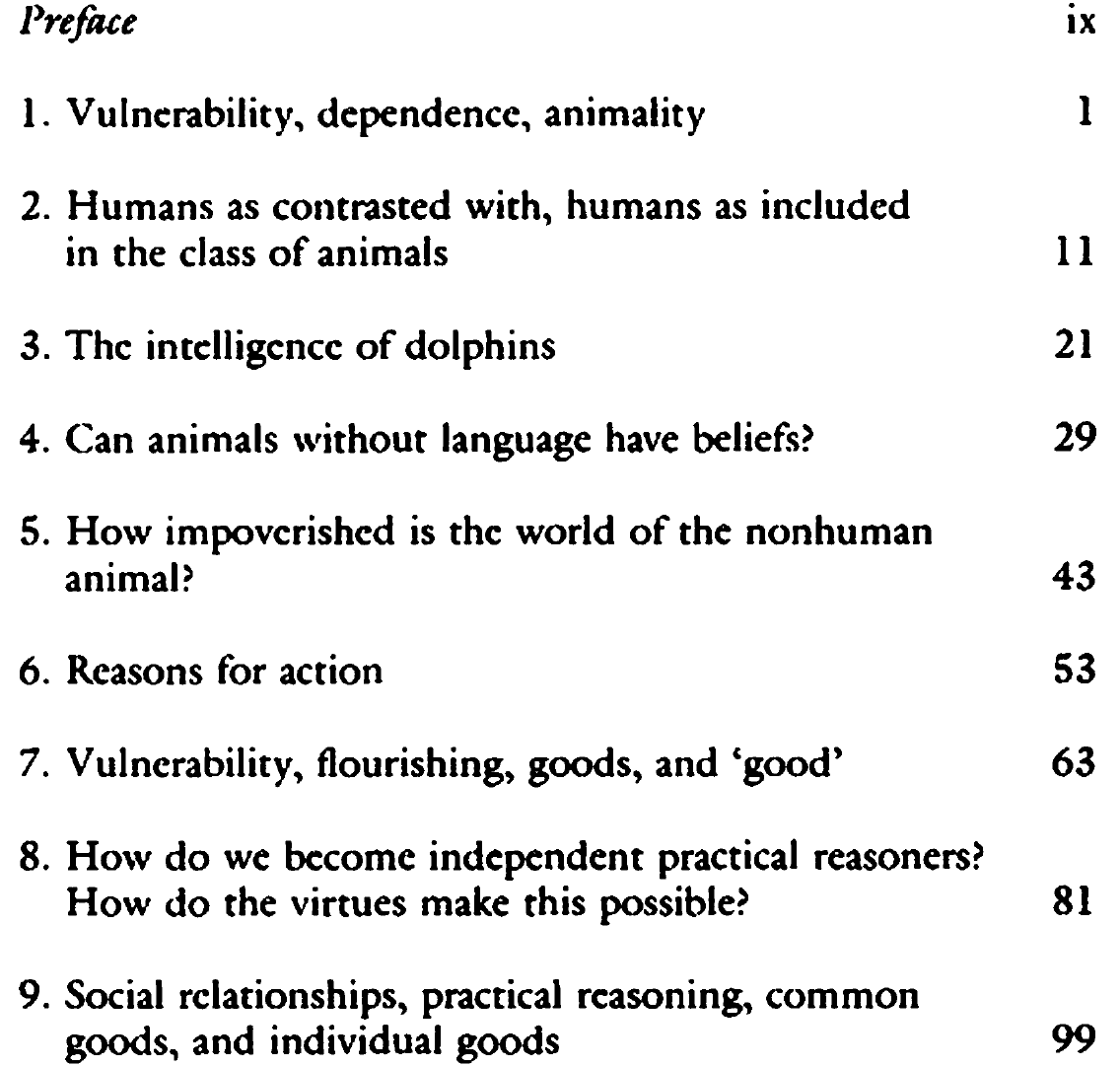查尔斯·泰勒的著作往往厚重,麦金太尔倒总是举重若轻。《依赖性的理性动物》这本小书从标题开始就无一字赘辞:“依赖性”,“理性”,“动物”性,三者同构了该书主题。
尤为难得的是,麦金太尔始终是位公开明确地进行自我修正的作者:“我似乎正在从事一项修正性的工作,……那个未能认识到上述问题的重要性、我给予纠正其错误和局限的哲学家恰恰是我自己。因此本书不仅是《追寻美德》、《谁的正义?何种合理性?》以及《三种互竞的道德探究观》的延续,也是对我在这些研究中一些观点的修正。”(p.x)[1]

如果我们与动物性(animality)的距离远不及我们所相信的那么大,如果我们也不似自己想象的那般自主、独立,而是充满脆弱(vulnerability)和依赖(dependence),我们还能如何设想自己是拥有美德并践履美德的人?与之相应,我们对哪些特质是美德的理解又将发生何种变化?
这些疑问恰是《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一书的出发点和主要论题。令读者感到安慰的是,该书且破且立,前九章铺垫了依赖性美德的种种构成性前提,后四章则直接回答了“承认依赖性的美德”(virtues of acknowledged dependence)是什么,以及能够支持这些美德的制度、社会结构及人际关系基础何在。
考虑到直接界定何为依赖性美德的章节包含一些值得参与的真正道德哲学论争——例如情感和同情是否涉及“应当给予”的问题,并从而服从于相应“给予和接受的规范”(pp.115-6),或是仅限定为道德心理机制,而此前的八九两章涉及对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值得详尽检视的精微观察,我的笔记相应拆分为三篇。本篇聚焦于前七章。
尽管作者第一章开篇只说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在幼年和老年格外明显”,而在人生中间阶段的依赖性与“受伤、疾病以及其他无能为力的情况”有关(p.1)。但事实上,麦金太尔在此的真正焦点却在于我们“成为独立的(independent)[2]实践推理者”的途径与我们的依赖性(dependence)之间的关系:
既然每个人类个体都不可避免地依赖养育者以“超越”自身“最初的动物状态”并“迈向人类特有的状态”(p.91);不仅如此,而且并不“存在一个点,在那之后我们就完全不再依赖他人”(p.97),甚至可以说“直到生命结束,我们都一直需要他人在实践推理中支持我们”(p.96)。这样一来,我们的依赖性就无关乎我们在能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强弱状态,而成为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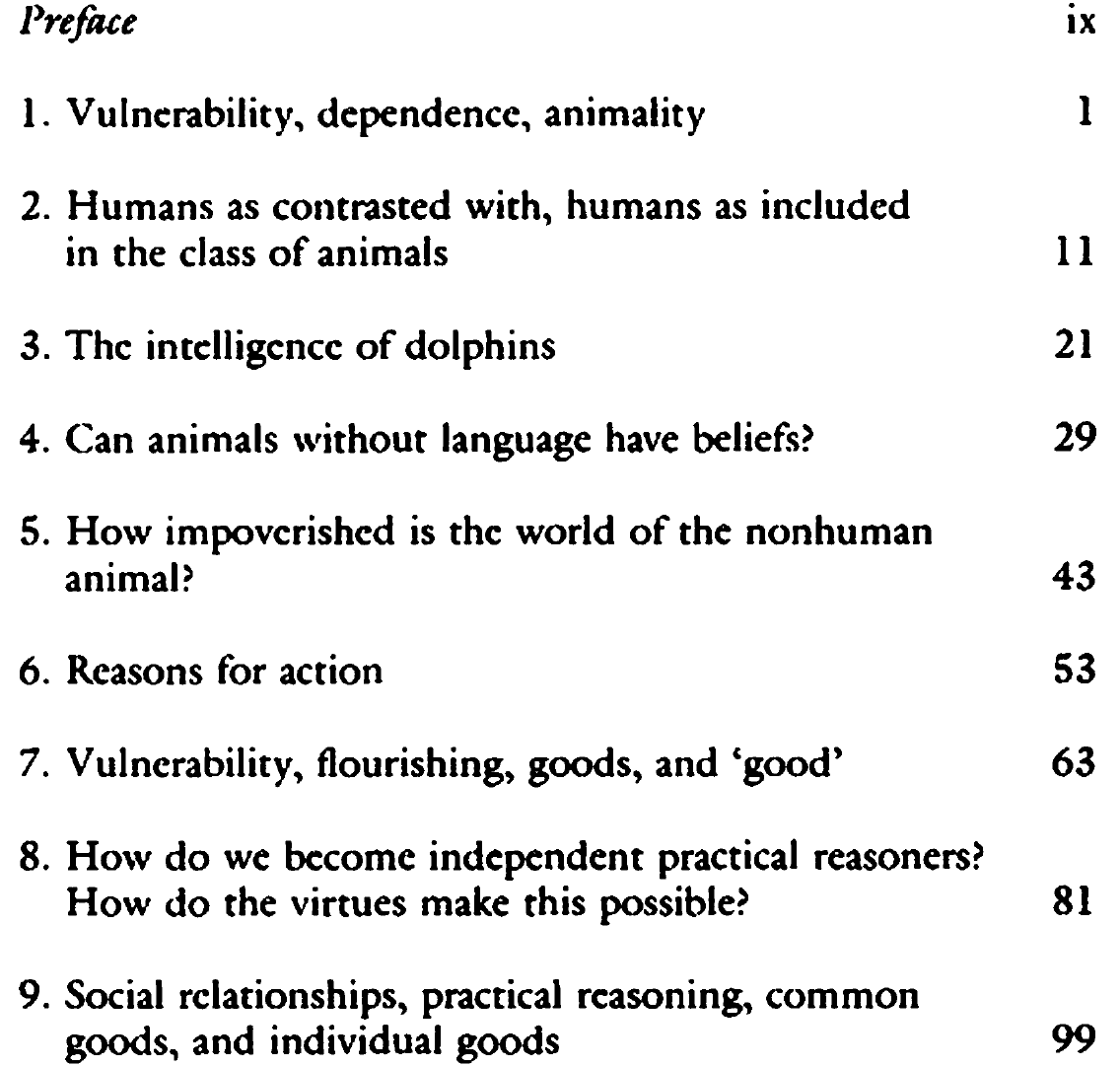
不过本书另有一论证负担,作者试图强调我们的依赖性和动物性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不仅不能使得我们独特,而且也不是践行实践推理的充分条件:一方面,没有语言能力的智能动物也可“通过经验改进区分、修正信念”(p.38),人类有所进益的能力仅在于“获得语言”并由此“能够以某些新的方式描述和反思前语言和非语言(nonlinguistic)的区分”,但毕竟这不足以割裂我们的人性与动物性,因为“在前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有着重要的连续性”(pp.36-7)。
另一方面,使得作为人的我们能够发起“行动”(actions)而不仅只是“运动”(bodily movements)(p.22)的决定性机能,是存在于前语言的生活经验中,而非语言中,即“要想充分理解某种语言在特定场合的意思,一个人必须至少具有相关社会实践参与者的某些能力”(pp.30-1)。
而至为关键的是,拥有语言并非拥有信念或欲望等“意向性状态”(p.35)的前提(第四章)。正是针对这一论点,作者重申人类的“一些信念”与某些非人类物种的信念在两方面的相似之处,它们基本对应着上述讨论中对语言动物的两重打击:
其一,人类的一些信念如同其他智能动物的信念一样“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表现在人同样只是怀有这些信念并“无反思地(unreflectively)或前反思地(prereflectively)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之中”;其二,即使我们使用语言并从而“具有反思性”,却依然依赖前语言的“那些认识、区别和对感知性关注的运用”(p.40)。
总之,无语言的智能动物拥有“通过认识、信念和对信念的修正、意图进行活动”的能力,也拥有“前语言的行动理由”,而人类进一步拥有“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给出的行动理由”(p.51)。麦金太尔援引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在关于行动理由的讨论中承认其他物种成员也拥有“自然的明智”——这使得它们尽管“不具有理性能力”,但却“拥有行动的理由”(p.55)。
无论如何,正是行动理由构成我们通向“理性动物”的关键。实现“从仅仅是潜在的理性动物向实在的理性动物的过渡”(p.56)主要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拥有语言才可能实现”:
1) 学会比较各种行动理由,即比较一种“好”和另一种“好”,从中选出“更好的”。这要求人类幼崽学习“对之前指引行动的理由做出反思并形成判断”(pp.56-7)。换言之,要“从仅仅拥有理由发展到能够评价理由的好坏”,并由此能够“改变行动的理由”,甚至进而改变其行动(pp.71-2)。
2) 学会辨别“正确的实践推理”与“良好的动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为了推理正确和动机良好而做到“与欲望保持距离”(p.73)。这涉及政治哲学中围绕个体真正的利益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论争,麦金太尔对此强调:“虽然大体上说,我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但是在对我来说什么是好的或最好的问题上,在许多重要方面我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更有权威”(p.71)。
至关重要的是,独立的实践推理者(independent practical reasoners)不仅仅要独立于他人(即摆脱对他人的完全依赖),还要独立于自己的欲望。这是柏拉图以降的持久辩题。麦金太尔在此的焦点是须独立于欲望的支配,令“那些迫切的需要不再像独裁者那样支配”自身,从而能够真正区分“好的行动理由”和“最迫切地感受到的需要”(p.69)。
这并不是要变得“没有欲望”,而是要“变得可以思虑其善好”(p.70)。在这一意义上,第二方面是第一方面的重要前提。
3) 学会对未来有所意识。更确切些说,这一方面所要求的转变是“从仅仅有对当下的意识发展到对想象中的未来有所意识”(p.74)。通俗些说,这里所要求的想象力、时间感和未来感要求我们在成长中学会思虑长远,这种避免短视的要求在将第三方面与前两方面结合来看时更加明显。
麦金太尔恰恰认为,第三方面与前两方面密切相关,因为恰当比较和评价诸多好理由,以及正确地节制欲望,二者都需要注目于未来:“当某人问自己认为某个行动的好理由是不是足够好时,它通常必须要考虑……还会有哪些未来的可能性”;“学会如何让自己脱离直接的欲望……也需要理解不同的未来给了我们哪些欲望对象和好”(p.76)。
在直接讨论依赖性前提下的美德德目之前,这三个要点是该书前三分之二篇幅中最重要的论证,值得多做些澄清。
就三方面的关系来说,第三方面可以看作描述前两方面的另一视角,缺乏对未来较为长远的思虑的人,也就很难形成对诸善的恰当反思和判断,也很难做到节制欲望。更笼统些说,则三个方面“都在同一个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三者中的任何一方如果出现严重失败都很可能导致或强化其他方面的失败”(p.76)。
如果要进一步追究它们为什么容易失败,不难看出第二方面的主要挑战是知易行难。区分“表达或报告有关自身需要的判断”和“关于什么对我们来说好或最好的判断”(p.70)似乎不易,但与其说我们难以辨认它们,不如说我们很难愿意搁置眼下迫切的欲求而服务于一个渺茫的在未来或许会降临的“最好”选项。
真正对认知构成挑战的是第一方面中如何区分识别不同的“好”,麦金太尔对此提供了一些精细的努力,认定我们“至少有三种将好归于某物的方式”:一是“将某物仅仅当作手段而称它为好”,二是“被视为因其自身之故值得追求的目的”的好。这种二分是老生常谈,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熟稔,后一种好还被进一步描述为实现活动,即“在实现特定实践的好中达到卓越”。(p.66)
第三种判断使得此处的讨论颇具价值,这涉及具体生活处境中的“好”:即“某种具体实践的好”就其在个体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言是不是对该个体好的?就其在共同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言是不是对该社会好的?换言之,“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怎样才能最好地安排生活中的好所做出的判断代表了将好归于某物的第三种方式”。恰是在第三种——而不是第二种——判断中,麦金太尔认为,我们关切到了“人类幸福”。(pp.66-7)
隐涵于“理性动物”/“独立的实践推理者”的成长历程的三方面描摹背后难以忽视的另一并行线索,涉及实践推理者之间如何共处,以及尚不成熟、还不够独立自主的成长中的人类个体如何在依赖性关系中与相对成熟的关联个体互动。在这一意义上,学习独立与学习合作是同一过程:鉴于我们自出生起、“甚至在出生前”即已深深涉入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的过程,亦即学习如何在“形成和维持”社会关系时“与他人合作”(p.74)。
参考资料:
[1]所标注页码为英文原著页码,即中译本页边码。如未另行说明,我的供稿均如此处理引文出处。
[2]在中文里我们可能会对“独立”(independence)与“依赖”(dependence)之间的语词对立不够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