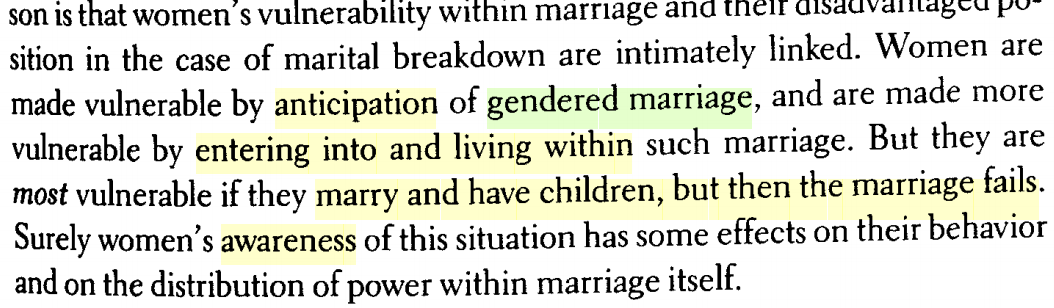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奥金(Susan Moller Okin)初版于1989年的《正义、性别与家庭》是将性别不平等问题引入正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此书挑战了公共领域-家庭领域之间的古老划界,明确主张在正义问题上,家庭这种社会制度正如其他各类基本社会制度一样:对家庭来说,正义同样是一种有着“根本重要性”的美德(a virtu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这就明确挑战了那些认为在有着温情关系或密切纽带的共同体成员之间不适于运用或者没必要运用正义原则的观点【1】,也就揭示了既被内帷私事与个人隐私的名义所遮蔽、又被公域和公器的无为无能所放任的不公甚或罪恶。
1. 聚焦于第七章:婚姻带给女性的多重脆弱性
该书第七章集中讨论了婚姻制度导致的性别不平等和女性易伤性(vulnerability),值得家庭危机多发且制度救济薄弱的社会中的各类读者严肃阅读。(从众从俗,以下仍把“vulnerability”译为不太准确的“脆弱性”。)
女性在其生活和生活预期中注定遭遇这种脆弱性,是因为家庭和婚姻中的生活安排是性别化的(gendered)。这不仅导致了家内权力的失衡,而且导致了女性个体在各自的人生早期就因为他人及社会对她们未来生活的刻板期待而遭遇自我发展限制。引用作者本人在该章中的概括【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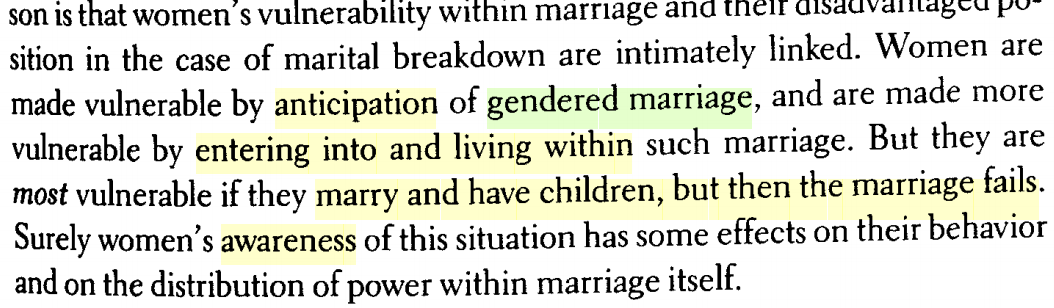
1. 女性因性别化婚姻(gendered marriage)的预期而被迫变得脆弱(vulnerable)。
2. 进入这样的婚姻并在其中生活,使得女性更为脆弱。
3. 如果女性结婚,又生子,其后却婚姻破裂时,她们最为脆弱。
4.单单是女性对上述境况的觉察,也会影响她们的婚内行为,影响婚内的权力分配。
对这四个层次的洞察缺一不可,此章内容本身也正是围绕这四个层次展开。在现实中,它们恰是层层叠加,形成令个体人生陷入困境的逻辑闭环——从对未来生活的有限可能性的预期开始,一步步陷入越来越别无选择的屈从地位,并且越是清醒就越是自甘认命。
2.女性如何陷入弱势而又难以改善境遇
本章直接援用的理论基础,其一来自道德哲学家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强调人类社会中即使从源头来看貌似“自然”的弱势,也实质上具有社会性特质。而在那些明显由当前社会制度创造、形塑和维持的强势-弱势关系中,本应受到保护的弱势方,反而总是更容易受剥削。在这种境况中,我们就不仅仅应当保护弱者,还应减少或消除那种弱势状态。
另一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家艾伯特·奥图·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其重要洞见是,衡量一种关系对等与否,可以看双方退出这种关系的相对能力。赫希曼原是用这种思路来分析各国间贸易关系中的不对等依赖,奥金则认为相关原理也适用于分析婚姻。
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读者可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本章无非是要谈论无酬家务劳动和女性职场-家庭双重工作负担的老调。但,哪怕考虑到本书完成于1989年,也会发现作者的观察既入微又根本:
她认为,根本困境恰在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信念。这根本性地导致了男性的家庭责任和家庭贡献实质上与他的职业追求和社会成就相一致,而对女性来说,她的家庭职责与她的事业期许却永远处在拉扯和矛盾之中。
通俗来说,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这样的问题,对女性构成性别歧视。但背后更实质的二分困境其实是:追求事业的同时赚钱养家,是对家庭的一类贡献;从事家务和后代的抚养教育,是对家庭的另一类贡献。在前一种贡献类型中,原本就不存在“平衡”问题。所以,批评“平衡事业与家庭”之论时,有必要重新评估以及重新安排家庭分工与家庭贡献的类型,较为彻底地克服主外—主内二分法。否则只能流于肤浅的敌视和对立。
由此,作者的一个精微观察是:“迄今,职业资产(career assets)上的投资是大多数夫妻或伴侣所拥有的最具价值的财富。如果妻子只是兼职工作,或者时而工作时而不工作,她们自身的职业潜能就会萎缩,开始极度依赖丈夫的职业资产。”【3】 这样一来,一个延伸问题就是,只要离婚法庭还倾向于把男女双方看作“平等”主体,资产处置就不可能是公正的。换言之,男方净身出户这种事,根本不该有什么道德光环,因为最具价值的职业资产恰恰根本不可能被转移或被剥夺。而在婚姻存续的过程中,只要意识到职业资产的不平等发展状况和由此产生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任何温情背后的权力关系都会伴随着支配和服从。
人们常说,一个人自身的内在能力,不可能被任何人夺走。那么,似乎女性只要能在婚姻家庭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能力和作用,按理说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安排与现行社会标准叠加,却取消了这种可能性:概括来说,一个根本的现象是,“唯一影响婚内权力的资源(resources)——诸如收入、成功、声望等——恰就是那些在婚姻之外的世界所看重的资源。诸如家庭服务、分娩和育儿方面的能力、技能和劳动等,这样的资源不仅与婚内权力没有积极相关性,而且实际上还有消极相关性。”【4】
即便如此,人们仍难免认定,现代女性还有一条兼顾内外的正能量之路。但社会标准又一次扮演了苛刻的“劝退”角色,即使女性自始至终重视职业发展,也仍然在社会安排面前无能为力。作者对此另一个更透彻、更根本的精微概括是:就整个社会的职场安排而言,“她们在工作上处于不利地位(disadvantaged),是被这样的事实造成:付薪工作(wage work)的世界……很大程度上仍旧是按照‘工作者’都有驻家妻子的假设而建构的”【5】。换言之,女性(或者任何性别的任何具体个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达成相当的职业成就,放弃家庭规划或牺牲家庭成员的家务福祉仍然不够,还需要获得积极的相当于“妻子”功能的生活支持才行。
3. 此章与此书的当下意义
在上述整体背景下重新审视对家庭职能和家务劳动的社会性轻视,才有望更彻底地在“职场弱势和家内不平等的恶性循环”的意义上反思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在这一意义上,严肃而细致地对待本书本章的论证,不仅有助于一般地理解现代职业女性的生活负担和人生困境,而且有助于针对性地理解“半边天”式的社会责任期许为何仍无法确保女性解放。
而本书也清楚地表明,相应的改善不可能寄希望于弱势个人的觉醒,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强势个体的自律和善意。社会制度的卸责(例如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对男性和夫家的制度性纵容)即构成不作为之恶。
本书初版距今逾三十年,在人类文明中的一些社会,书中条分缕析并激发人们进一步反思的那些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尚未普遍讨论,甚至尚未充分提及。
2020年的祖国大地上发生了不少无妄降临在一些女性同胞身上的悲剧甚至惨案,而真实且持久的强势-弱势支配关系则更无处不在。可惜的是,在对大量性别议题(例如去年年末最高法院发布的对生育权问题的最新解释)的当下热议中,并未见我国学界有超过苏珊·奥金水平的评论。
更加不幸的是,此书中译本实在是错误太多——这是此书常年占据我打算下手重译的书单中前三名位置的原因。读书人的最基本职责是准确传达信息,而有些学者确实不具备必要的相关能力。
注释
【1】不过此处值得说明的是:这对桑德尔的挑战要比对罗尔斯的挑战更大。且两类挑战实则基于不同理由。
【2】原著第167页,中译第239页。
【3】原著第156页,中译第220-221页。
【4】原著第157页,中译第222-223页。
【5】原著第139页,中译第192页。
参考文献
1.Susan Moller Okin (1989),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2.苏珊·穆勒·奥金(2017),《正义、社会性别与家庭》,王新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7R4McLvJBe_eZEmXsGLTg